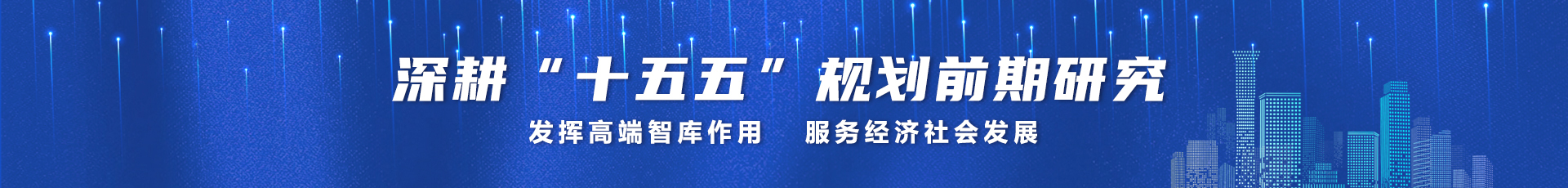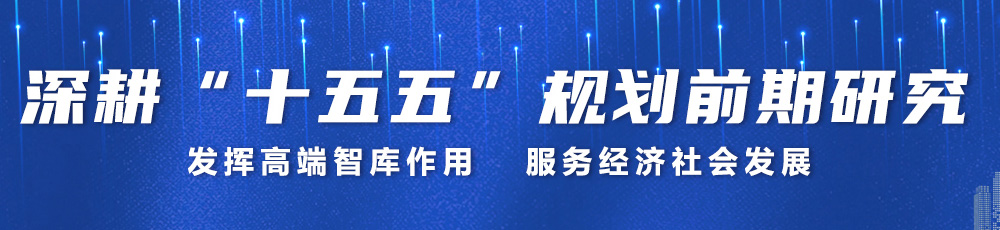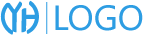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科研应纳入科学伦理治理体系
5月7日,中央文明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》(简称“意见”),要求网站平台“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”,这是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又一项重要政策,将进一步优化网络生态环境。
近年来,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,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,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。但在其快速发展进程中,“瘾性”数字经济逐渐浮出,为数字经济治理带来难题与挑战。
“瘾性”数字经济危害大
所谓“瘾性”数字经济,就是由供给者提供消费高频且容易产生依赖的“成瘾性”数字产品及服务,由受众广泛、难脱依赖的“上瘾者”高频次、非理性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,往往活跃在网游、短视频、直播、网购、在线社交等数字经济领域。
“瘾性”数字经济因其能够对生活、生产带来智能与便利,以及丰富的体验与高效率,本身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,也因此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,但这并不能掩盖其“瘾性”的危害——
一方面,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。从医学角度看,消费“瘾性”数字产品,会对人中枢神经产生持续且高强度的刺激,长期沉迷会产生疲劳、焦虑、忧郁、暴躁、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问题,2019年9月,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网络游成瘾认定为新的精神疾病,列入了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。
另一方面,“瘾性”数字产品与服务引诱消费者产生大量非理性消费,各类数字产品及服务往往通过“免费推广”模式带入消费者后,就开始通过花样繁多的付费项目“割韭菜”,已“上瘾”的消费者往往会产生大量非理消费行为。
而从全社会层面看,“瘾性”数字经济诱发全社会“成瘾性”消费,为社会生产力带来隐性的破坏,增多了社会犯罪、危害治安的诱发因素。
数字经济“瘾性”的形成,根源是供给者的商业贪婪,手段是隐蔽的技术研发。数字经济普遍通过精准“算法”完成“瘾性”的技术设计,从而精准、定向地俘获消费者并使其产生消费依赖。
“瘾性”数字经济治理难
有着明显“瘾性”特征及严重危害后果的毒、赌、黄等供给和消费都被界定为非法,而对于烟草等合法“瘾性”商品,其供给侧有着严格的专营管理体系,其需求侧也有倡导戒烟、公共场合禁烟等干预措施,而“瘾性”数字经济在供需两端都存在治理缺失。
从需求侧看,由于消费合法的“瘾性”数字产品与服务是出于个人意愿,且全社会对其危害性认识显然没有上升到足够的高度,加之“瘾性”数字产品与服务界定模糊,当前甚至没有像倡导戒烟、公共场合禁烟一样的治理干预措施。
在供给侧看,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力度,但治理体系仍有不足。2021年9月《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工作的通知》出台,但该政策其仅针对“瘾性”特征相对明显的网游领域,政策保护对象也仅针对未成年人,对其他“瘾性”数字经济领域及成年人群缺乏效用。
在2021年12月底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》,主要针对“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”,其政策手段主要是“进行算法备案与”“安全评估”等,未能覆盖具有“瘾性”特征的诸多数字经济领域,对于其隐蔽且复杂的“瘾性”导向技术创新难以有效对治。
上述“意见”已将“瘾性”数字经济治理领域上从网络游戏拓展到网络直播,但仍然不能涵盖“瘾性”数字领域的全部,政策保护人群仍为未成年人,成年人的“瘾性”沉迷问题仍无相应举措。
健全“瘾性”数字经济治理体系
鉴于当前“瘾性”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不足,在国家着手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之际,结合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部署,可考虑将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的科研活动纳入到科技伦理治理体系,从科研技术源头上鉴别与消弭数字经济的“瘾性”,推动数字经济的科技求真与伦理求善。
一方面,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的科研活动成果会危害人的身心健康,这明显适用于今年4月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的政策范畴,适用于“科技活动应最大限度避免对人的生命安全、身体健康、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潜在威胁”的政策条款。
另一方面,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的科研活动广泛应用了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,在其科技伦理识别、技术影响鉴别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,将其纳入科技伦理治理体系,借助科技伦理体系治理的资源与规范,在其科研技术源头上进行规范与限制,才能把数字经济的“瘾性”关在笼子里。
当然,这首先需要完成诸多基础工作,包括但不限于科学界定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外延,准确界定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科研活动特征与类型,明确提供有价值的数字产品与控制其“瘾性”的均衡原则,确立限制“瘾性”科研技术应用的边界范围等。
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研究相关措施,推动“瘾性”数字经济科研活动纳入科技伦理治理体系。同时,相应增加需求侧管理,倡导理性、健康的数字消费观念与方式,净化数字经济消费环境,消弭“瘾性”数字消费的危害,推动数字经济健康、快速、可持续发展。
(作者:投资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李道今)